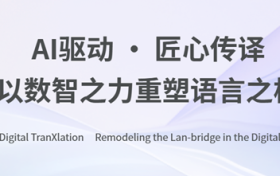最近几天,一条关于北大发在《Science》子刊上的基因编辑技术论文的新闻火了,这条中文消息称北大团队实现了“精准”“特定”记忆删除,引发了各种乱七八糟的舆论联想和莫名其妙的恐慌……
记忆真的可以删除吗?今天我们来探寻真相。
实际上北大发表的这篇论文本身是在汇报一次动物实验中的技术进步,只是在实验当中选择了改变与恐惧和学习功能相关的脑细胞基因,他们的目标是采用改良基因编辑技术更方便的建立动物模型,而不是想对人类的记忆干什么……

改变脑细胞的基因表达是本次研究的首创吗?
其实我们早就有改变大脑神经细胞基因表达的常用医疗手段了,比如反义寡核苷酸和RNA干扰就被常常用来沉默大脑中的某些基因,且用到了具体的临床治疗上。
就神经疾病治疗来说,此前已经有使用反义核苷酸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方案——2006年就有美国加州大学团队发表成果,采用这种方法来改变大脑和脊髓中SOD1蛋白和mRNA的水平,来改善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的病情。这个方向上FDA和EMA都已经批准上市了一些药物。
常见的其他神经疾病,比如亨廷顿病,目前反义核苷酸治疗的临床试验结果也是比较有希望的,近些年也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最近《Science》也发表了一篇观点性的文章,总结了这一治疗手段在神经疾病方面的进展,可惜遐想空间较小,没有引发太多舆论关注。
那么,既然改变脑细胞基因的成果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临床上开始治疗人类患者的神经疾病了,为什么北大团队还要使用基因编辑手段再去尝试呢?
因为上面这个方法在大鼠和非人灵长类身上不好用……尤其是转基因大鼠身上。北大团队改进基因编辑技术是为了更高效的建立动物模型,这个理由在论文的开篇部分已经阐明,相信如果能从开头读一读这篇论文,不至于产生很多意味不明的联想。
本次“精确删除记忆”的操作到底是啥?
如前所述,即使已经用于临床研究的反义核苷酸治疗,在大鼠尤其是转基因大鼠身上并不好使——动物神经疾病模型制作本就不容易,包括神经损伤后的行为测验等等都与人类存在差异——再加上一些已有的技术存在准度问题,不能准确定位大脑的特定功能细胞,因此北大团队设计发明了一种改良的基因编辑手段CRISPR-SaCas9——采用了来自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的SaCas9替代了之前的化脓链球菌(Streptococcus pyogenes)SpCas9,来提高对特定功能细胞的定位准度和沉默特定基因的效率。
为了确定新工具对特定功能细胞有效,研究组选择了与恐惧记忆有关的功能。文中主要的研究指标还是DNA表达变化的分析,包括对CRISPR常见的脱靶问题的解析也来自对编辑后基因的直接分析——分析显示脱靶问题仍然存在但是较之以往的技术,脱靶位置少了许多,情况大有改善。
深受社交网络舆论关注的删除特定记忆的部分是研究中的行为学测试部分,研究采用了条件化情景恐惧训练(context fear conditioning, CFC)来测试基因编辑是否成功影响了目标功能细胞。CFC是一种经典的动物行为模型,主要是使动物对特定条件情景产生恐惧,然后通过观测动物的木僵(freezing)水平来确认神经功能的改变或其他条件的变化。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CFC是AB两种对照场景,流程大致如下——
首先在起点给实验用大鼠进行药剂注射(注意这时候还没激活SaCas9),3周后进行AB两种不同的CFC训练,2周后先把大鼠暴露在环境A中,然后送回笼子里,给大鼠Dox用于激活SaCas9表达,1天后把大鼠暴露于环境B中,最终1周后测量大鼠在唤起A和B环境回忆后的木僵水平。
结果显示,大鼠在环境B当中的木僵水平较环境A降低了一些,如下图——
左边的柱状图显示的是给大鼠Dox当天AB环境暴露程度引发了同样的木僵水平,右侧则是激活SaCas9表达之后1周,再进行CFC测试时的情况,其实大鼠对环境A和环境B的木僵水平都出现了下降,但是B下降更多,证明环境B被大鼠遗忘得更多。显然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过去,大鼠对环境A得恐惧情绪也出现了自然的下降,木僵反应水平下跌了,而对环境B的木僵水平下降更多说明基因编辑起效了,但是木僵也并未完全消失。
总之,论文本身和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表达的信息和由此诞生的联想不是一回事。
关于操控记忆的动物实验
现在回头再来说一说这么多人担心的“删除记忆”实验,其实这种关于“学习-恐惧-回忆”的动物实验,尤其是以CFC为研究基础的动物行为实验早就存在了。
神经学家对涉及到记忆的大脑区域的研究早已有之,通过破坏、刺激甚至销毁实验动物目标脑区来影响记忆的研究也非常之多,CFC是研究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以及海马体记忆功能的重要行为范式,作为一个基本方案也有许多的争论和校验。
比如说CFC的暴露流程如果出现一些改变,就可能导致最终动物的木僵水平发生极大的变化,而如果动物的学习能力受到影响,影响它对环境出现习得性恐惧,也会对最终的木僵是否出现产生影响。
因此北大的这项研究中直接的DNA分析以及其他分子水平的检验手段也是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学实验结果其实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较多的一种检验手段——但是因为比较直观,反而被媒体重视。
至于通过操纵记忆最终显示在木僵水平的改变上的研究,那就太多了。
1992年,Kim和Fanselow采用CFC训练动物,分别间隔1天、7天、14天、28天电损毁实验动物的背根海马,发现间隔1天后损毁背根海马会彻底破坏习得的情景恐惧;但是,间隔28天后损毁背根海马基本对情景恐惧无影响。
从行为学结果上和北大这项研究相近的研究也有,比如1999年有人采用了类似方案:在情景A内对动物进行CFC训练,50天后又将动物放入与情景A完全不同的情景B内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第二天电损毁背根海马,恢复一周后分别将动物放入情景A和情景B内测试。发现动物在情景B (近期情景恐惧记忆)内表现出的木僵只是对照组的1/3,而动物在情景A (远期情景恐惧记忆)内的木僵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这项1999年的研究证明了背根海马的损毁只会对近期的情景记忆产生影响,并不影响远期记忆。
1999年的这项研究如果赶上了“标题党”,恐怕也是“删除特定记忆”了。
从20多年前到今天,CFC已经从验证大脑特定组织的功能到今天用于验证大脑分子层面的改变,人类对大脑的认识随着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努力,在不断的进步着,当然也还有许多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看到特别耸动的报道消息,去核实一下研究原文也是好的,既能搞清一些问题减少一些无意义的联想,也能增加一些奇怪的知识嘛……